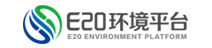承包不應是唯一解決辦法
| 論文類型 | 基礎研究 | 發表日期 | 2004-03-01 |
| 來源 | 中國水網 | ||
| 作者 | 李仕林 | ||
| 摘要 | ——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市場化改革制度設計置疑 李仕林 近兩年,國家主管部門對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市場化改革的制度設計框架正在逐步成形。各地也基本上正在按照這套制度設計框架實施改革。在筆者看來,制度設計中提出的各種解決方式可以用“承包”予以概括。但筆者認為,承包不應是唯一解決辦法,謹提出一 ... | ||
——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市場化改革制度設計置疑
李仕林
近兩年,國家主管部門對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市場化改革的制度設計框架正在逐步成形。各地也基本上正在按照這套制度設計框架實施改革。在筆者看來,制度設計中提出的各種解決方式可以用“承包”予以概括。但筆者認為,承包不應是唯一解決辦法,謹提出一管之見參與討論。
對這項制度設計給予最詳盡闡述的是國家環保總局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撰寫的文章《我國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與運營市場化問題調研報告》(見《中國環境報》2003.1.29~2003.3.14)
這項制度設計認為,在城市環境基礎設施的投資方面,“政府必須發揮主導投資作用,市場化方式為輔”;在設施運營方面,“可以逐步全面實行市場化運作方式”;在總體進度上,東部地區可以按上述方式“全面推進”,西部地區“要有重點有步驟逐步推進”。這些就是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制度設計中的核心問題。它們決定了這項市場化改革的主要特征。其中,投資主體又是核心中的核心。這里雖然提出的是政府“主導投資”,并未講政府是“投資主體”,但是整個制度設計都沒有限制政府直接進入市場,更沒有限制政府成為投資主體。從整體上看,各地的實踐大多將政府作為了“投資主體”。既然政府是投資主體,政府必然就是城市環境基礎設施的產權主體,圍繞這個主體進行的市場化改革的各種形式可以用“承包”予以概括。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工程的招投標也好,已建成設施運行權的承包也好,BOT也好,都不是投資體制的改革,因而也不是產權制度的改革。
筆者認為,承包是對計劃經濟體制的重大突破,但不應該是改革的唯一方式。
一、 必須改變政府作為唯一投資主體的制度設計,更必須改變政府作為直接投資人的制度設計。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二十多年了,我們已經弄清楚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基本關系。政府只能是市場制度的設計人和市場秩序的監管人,而不能同時成為市場中的經營者。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曾經大量使用的承包方式,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打破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是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一種形式,但其本身并不是市場化。在中國已經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今天,如果只把承包方式作為改革的唯一方式,那么,在推進改革的同時,也會對改革起到限制的作用。
筆者承認,在中國的現階段,尤其是在我國大量興建城市環境基礎設施的起始階段,政府的投資需要發揮主要作用。但這并不等于政府要成為直接的投資人,更不等于政府要成為經營者。政府的投資應該通過國有企業或者國有股份以“國有資本”的身份進入市場。這里的“國有企業”不應該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而應該是經過現代企業制度改造后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這樣的國有資本應當與其它有可能進入這個市場的非國有資本享有同樣的市場待遇,即,它可能保值增值,也可能會有風險。
在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市場化改革制度設計之初,曾經設想,我國高達數萬億的民間閑散資本和大量的國外投資會涌入這個市場。我國環境保護“十五”計劃規定,“十五”期末,全國城市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率要達到45%以上,50萬人口城市要達到60%以上,全國需要興建1000多座城市污水處理場,總投資在1000億以上。而各級政府可能投入的只是小頭,大頭需要靠非財政資金。但是,幾年過去了,民間閑散資本和國外投資并沒有大量涌入這個“市場”。原因何在?筆者認為很簡單:這個“市場”并不存在。
問題就出在制度設計上。制度設計的立足點是政府作為直接的投資人和經營者。如果沒有任何對于非政府資本的保障,無視資本在市場中的基本屬性,無論怎樣“鼓勵”和“號召”,非政府資本都是不會進來的。當然,另一種競爭正在各地激烈進行。民營企業作為承建商正在激烈角逐政府投資的城市環境基礎設施的招投標和已建成設施的承包運營權。很顯然,這不是民營企業的投資行為,而是對政府投資的經營行為。
這項制度設計十分推崇BOT,以及類似于BOT的其它方式。各地在推進市場化的進程中,也在大量采用BOT方式。但BOT的實質是政府向企業“借錢”,是一種融資方式,本質上不是一種投資方式。BOT的核心問題是政府用協議保證了企業投入的保值、增值和利潤,最終產權交還政府。這與市場中企業自主投資,自己承擔風險,有本質的區別。如果BOT成為中國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方式,市場化意義上的“市場”仍然并不存在。還應該指出,從市場化角度看,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BOT不可能創造最高的投資效率和運行效率,BOT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的主要投資方式。
這項制度設計沒有擺脫以全民所有制為主體建設城市環境基礎設施的思維模式,并且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國家對這些設施的控制權。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由于篇幅所限,這個問題難以在此展開。但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思維模式與民間資本大量進入城市環境基礎設施的期望是互相矛盾的。
二、 制度設計上的理論困擾
這項制度設計的理論依據是世界銀行對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市場化能力的一項定量分析。并且得出了“在設施建設方面,政府必須發揮主導投資作用,市場化方式為輔”的核心結論。
筆者認為世界銀行對環境基礎設施市場化能力的定量分析,是符合這類“公共物品”的客觀屬性的。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我國此類制度設計的上述結論。
世界銀行的分析指出了這類“公共物品”在市場化過程中需要更多的政府參與。而這種“參與”,是與彩電、冰箱之類非“公共物品”經營的市場化相對而言的。在“公共物品”的市場化中,政府需要對市場進行更多的管理和約束。更進一步講,企業受到的管理更多一些,自由度相對較小一些。但這絲毫不意味著,政府必須成為市場的投資主體,政府必須成為直接投資人和經營者。市場經濟比較成熟的發達國家,其城市環境基礎設施的市場化狀況,也完全不是上述制度設計框架所展示的那種情況。被我國環境界所推崇的“泰晤士河管理模式”的泰晤士河流域管理局,政府不僅不是投資主體,而且十多年前就已私有化了。其主要經營行為,受到法律的保護,同時也受到法律的制約。同冰箱、彩電之類“非公共物品”的市場化相比,企業受到的約束要多得多。但這并不意味著企業只能向政府搞“承包”,或者政府跑進市場去同企業搞競爭。
如果政府跑進市場,哪個企業還敢到市場去投資?
三、在市場化的實施步驟上,先東部后西部的制度設計安排,不符合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
在我國推進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市場化,從近期來看,至少需要達到兩大目標。其一,解決投資總量不足的問題。其二,解決投資效率不高和已建成設施運轉效率不高的問題。這些都是計劃經濟體制難于解決的問題。這兩大目標,對于相對貧窮而又急需大批建設城市環境基礎設施的西部地區都是迫切需要的。
三峽庫區及長江上游地區,是我國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地區,五個省市正在大規模地進行。從今年開始,陸續將有大批城市污水和垃圾處理場竣工。但這五個省市大多處于西部地區,目前基本上都未向市場化邁步。現在雖主要處于投資建設階段,卻已暴露出體制弊端帶來的諸多問題。可以預計,竣工投運以后暴露出來的問題會多得多。當一個城市的環境基礎設施不多的時候,用計劃經濟的辦法投資和運行,當地政府的財政力量是可以承受的。但是當一個城市或者一個省,大規模地普遍地建設城市環境基礎設施的時候,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五個省市目前的建設主要依靠中央財力的投入,但投資的低效益和運轉的低效率都會在建成以后迅速顯現出來。今年6月,三峽庫區蓄水已到135米水位。重慶市已建成的所有污水處理場,因管網不配套,沒有一個能達到設計水量運行,就是一個例證。四川省能正常運轉的污水和垃圾處理場也很少。其原因都可以在制度設計上找到。隨著竣工的污水和垃圾處理場越來越多,類似例子將會越來越多。
如果不盡快實施市場化,這五個省市的城市環境基礎設施仍然要在計劃體制的低效率下運行。對于相對不發達的西部省市來說,相當于越窮越要付出高價錢來改善環境。矛盾是十分突出的。其結果,要么加重當地財政負擔和居民負擔,要么因為體制上的種種弊端使已經建成的設施不能正常運行。此類個案已經不少。這對于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都是不利的。因此,筆者認為,西部這五省市比東部地區更需要盡快實施市場化。
四、 結論與建議
近幾年,尤其是近兩年,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正確地提出了推進城市環境基礎設施體制改革的問題。但改革究竟采用什么框架,是在計劃經濟體制的框架內進行改革,還是打破計劃經濟體制本身,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問題。“承包”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跨出了一大步。但承包不應是這項改革的終點,而應該是起點。
為了正確地推進這項改革,理論研究必須先行。理論研究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鼓勵百家爭鳴。如果沒有這個前提條件,我國環境保護的政策創新、體制創新和工作新局面都難以實現。
論文搜索
月熱點論文
論文投稿
很多時候您的文章總是無緣變成鉛字。研究做到關鍵時,試驗有了起色時,是不是想和同行探討一下,工作中有了心得,您是不是很想與人分享,那么不要只是默默工作了,寫下來吧!投稿時,請以附件形式發至 paper@h2o-china.com ,請注明論文投稿。一旦采用,我們會為您增加100枚金幣。